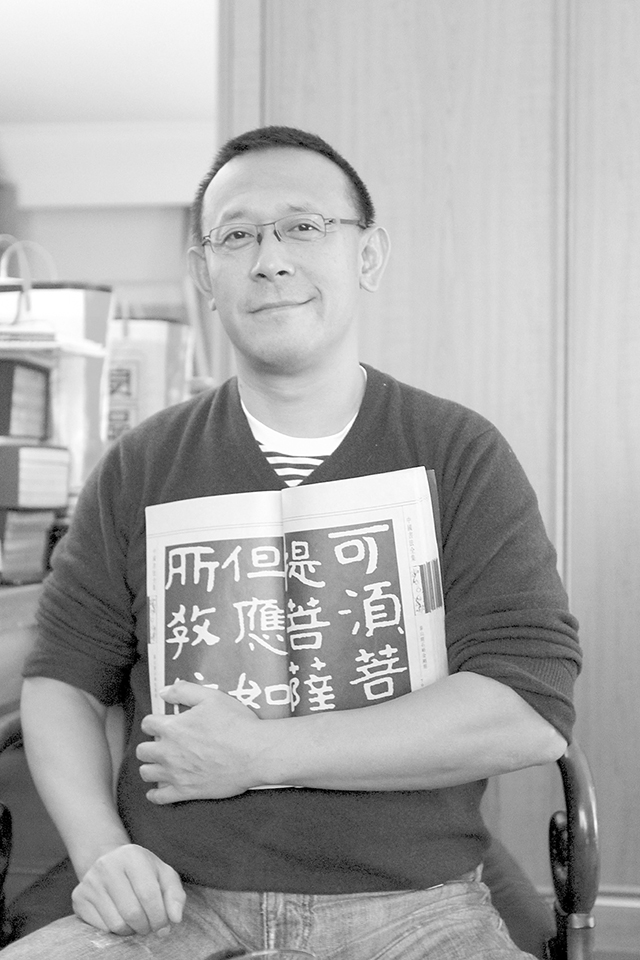
姜文坐在工作室里。 (资料照片)
上海国际电影节每年都会颁发一个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,能在中国电影的摇篮上海获这个奖,对华语电影人而言,是一个很特殊的荣誉。今年这个奖将在今晚的开幕式上颁给姜文。
近日,坐在北京不亦乐乎公司的办公室里,姜文和记者聊起他与上海的缘分。他的导演梦想缘起上海,激发这个梦想的,是谢晋。那一年,他23岁。谢晋在他心里播下的这颗种子,历经28年,已然枝繁叶茂,参天而立。
跟谢晋学做导演的毛头小子
1981年,姜文还在中央戏剧学院上学。那年谢晋筹拍《王昭君》,想找新人来演,便去中戏看演员。中戏当时的院长金山是谢晋多年老友,用谢晋后来的话说,“我要找王昭君,金山却给我推荐了一个毛头小子,瘦得像竹竿,叫姜文。结果我在那个班上挑到两个好苗子,男的姜文,女的丛珊。”那是姜文第一次见到谢晋。在他的记忆里,“大概是二年级的时候,谢导带丛珊去拍《牧马人》,说是《王昭君》不拍了。”但谢晋一直惦着他,4年后他找到毕业了的姜文,交给他一本《芙蓉镇》。
跟着谢晋来到上影,迎接姜文的是怀疑的目光,年轻、瘦弱、还老眨巴眼,这是《芙蓉镇》里那个饱经磨难沧桑的秦书田吗?他能跟大明星刘晓庆演一对吗?谢晋用的是激将法:“我就欣赏你,好好演,证明给他们看。”于是,姜文满脑子都是秦书田,他看书查资料、采访老右派、写人物分析、编角色小品……有一天在谢晋家演着演着,谢晋忽然说了一句:“你小子,将来是做导演的料。”
被谢晋“下放”到湘西王村一个月后,《芙蓉镇》开机。这时的姜文已经与村民没啥两样了。他天天跟在谢晋身边,陪他喝酒,看他拍戏,还大着胆子跟他要求摸摄影机。“谢晋是我做导演的领路人,我的很多工作方法其实都是从他那里‘偷’来的。比如他说选对演员就是成功了一半,对演员要欣赏要鼓掌,给他自信,放大他符合角色的那一面。比如道具、服装、化妆必须反复推敲提前到位,让演员开拍前就穿上,仿佛生活在角色里。
1994年,姜文的导演处女作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完成,他专程提着拷贝到上海请谢晋检验。谢晋在里面看,他却蹲在门外,“心里七上八下,比考试还紧张。”
从《让子弹飞》到《一步之遥》
姜文的工作室里,最显眼的是一张大桌子,“可以当饭桌,也可以开讨论会。”桌边的门框上,贴着一副不着四六的对联:“看洪波戴龙征宇楚楚云飞;听危笑思杨述平堂堂俊立。”姜文呵呵直乐:“我瞎攒的,就是把咱们几个编剧和工作室兄弟的名字都联起来。”那一阵,对联里的这几位天天和他没日没夜围着桌子讨论剧本,累了就拿名字逗乐,《让子弹飞》和《一步之遥》便这么开始了第一步。“其实这两个题材几乎同时在弄。”《让子弹飞》先拍,留了个结尾“浦东就是上海”,就因为要拍《一步之遥》。
《一步之遥》的故事发生在老上海,“知道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《阎瑞生》吧?就是在上海诞生的,划时代作品。那天我学弟史航说这个有意思,我就想起来了,学中国戏剧电影史的时候,有这么一出。现在老说商业电影,那会儿《阎瑞生》从拍摄到发行上映,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商业电影的鼻祖。这阎瑞生真有其人,我就查老报纸查老资料,发现围绕这个阎瑞生案,有很大的改编空间。”但姜文从来不会照搬故事,他和编剧们把素材掰开了、揉碎了再重新结构,反反复复,捏出了马走日、项飞田这两个人物,到最后发现和阎瑞生几乎已经没什么关系了。
在剪辑间里,姜文拿了立体眼镜给记者看正在剪辑的片断,一群洋人美女跳着踢踏舞,一个跟头“冲出”银幕。这片子是3D的,姜文介绍说用了刚刚研发出来的最新3D摄影机,“我是第一个使这机子的”,这让他有点小得意。
6月6日,在乌镇补拍了夏季的镜头,《一步之遥》宣布杀青。同时,该片的上映也已定档,选在了贺岁档的12月18日。
碰到误读,“要不要演姜文”
从香港电影节到威尼斯电影节到上海国际电影节,今年都安排了姜文电影回顾单元,因为从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诞生至今,正好20年。这么一算,姜文便又发感慨:“忽然成了老人家了。”在香港电影节的记者会上,也是这一句“老人家”,让他成了“倚老卖老教育记者”的“典型”。他自己也不明白,好好的对话,怎么就成了“教育”。
都知道新演员登台会“上场慌”,姜文说自己是每次要开记者会就“上场慌,犯怵。”他说,葛优有次打的,司机认出他说:“哎呀,你就是那个演葛优的呀!”笑过之后,姜文说,也许在观众眼里,角色和演员就该是一回事,姜文也就该是演“姜文”的那个。“被误读的感觉很奇怪。我能告诉他们吗?其实我很认生,打小怕和陌生人说话。”这个谜底属于演员心理学范畴,但他还真无计可施,只能一次次硬着头皮回答一些已被预设答案的问题,而他偏偏是一个不会顺杆爬的人,碰到误读,他还会较真。“要不要演姜文?”这还真是个让他很挠头的问题。
文汇报记者 陈晓黎